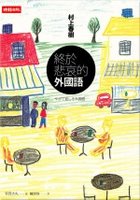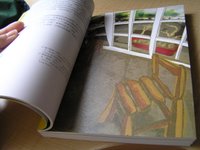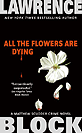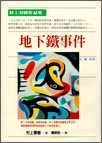蘋果日報2006年10月22日‧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今年七月,浸會大學頒發了第一屆「紅樓夢獎」,這是整個華文世界裡獎金最高的一座文學獎,專門頒給每年最傑出的華文長篇小說。香港入圍的作品就只有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它還得到了以哈佛王德威教授為首的評審團讚賞:「這是一部構思絕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間關係來構築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份又匠心獨運地寫出了香港這座城市特有的資本主義歷史風貌。其精妙的藝術構思和後設的寫作技巧受到了評委的讚揚……」所以董啟章得了一個評審團特別獎。
但是他沒拿到大獎,和最重要的三十萬獎金。其中一個理由是這本書只是他《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有待發展完成……
「我曾經想像自己擁有那三十萬港幣」董啟章如是說。身為他的朋友,我也很希望這筆錢是他的,而非賈平凹,完全出自鋤強扶弱的心理。我告訴他:「你知道嗎?賈平凹一本書的稿費和版稅加起來恐怕就不只這個數了。更何況他的書法也是值錢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飯館商號盼著他題字呢。」董啟章聽了不算吃驚,但還是不免羨慕:「唉!要是有三十萬,夠我用幾年了。」
這位全華文世界其中一位最傑出的作家,只要給他三十萬,還真能用上幾年。「我試過在一個月中旬的時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塊錢,覺得不大保險,於是跑去按提款機,但卻提不了款,原來我的戶口只剩下五十多塊了。」我和他一起計算了一下他的年度收入。就拿《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這本書來說吧,台灣出版(因為香港已沒有出版社願出長篇小說),所以版稅不錯,每本收取十元港幣;又由於它「暢銷」,賣了五千本左右,因此董啟章今年大概可以賺到五萬港幣,差點就能保證是最低工資的水平了。
我問:「你算是全職作家嗎?」「很尷尬,我的確是全職在家寫作,但是『職』這個字意味著有一份可以餬口的職業,事實上寫作卻又養不起我的生活。」
我認識董啟章的時候,他的日子過得還不壞。但在1997那一年他和黃念欣結婚了,接兩夫婦在粉嶺買了一間小單位,然後生了個兒子董新果。且莫說養大一個孩子要用四百萬(這是李麗珊在一個銀行廣告裡說的),光是買樓的供款就吃不消了。「我們幾個月前才研究過,原來六年下來只是在還利息,依然欠了銀行一屁股債。」所以他們差點又把樓給賣了,好在有親戚出手相助,才算渡過難關。
董啟章是個好爸爸,每天起床就帶兒子上學,然後做家務和寫作,下午再去他母親那裡把兒子接回來做功課。黃念欣現在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高級導師(還沒當上助理教授),收入勉強夠兩夫婦開銷。「我一沒錢就問她,所以我到處跟人說自己靠老婆養。她並不喜歡我這麼說,覺得我寫書是件非常棒的事。但事實如此,又有什麼不好對人說的呢?」
然而,說了這麼半天,這到底是董啟章自己的選擇,所以他也沒有埋怨什麼,反而自覺幸福。多年前,他開過一家公司,叫做「董富記文字工藝」(『董富記』是他祖父創辦的衣車零件小工廠),是香港最早也最有系統地教授創意寫作的組合,成員還有他的學生王貽興。近年教改,有許多學校找他們這種「外援」入校,所以有兩年他的收入算是穩定。當時他以為找到了一種平衡工作和創作的方法,可以每天教書改作文之餘繼續自己的長篇。辦法就是寫「組合式長篇」,以一小塊一小塊的零件段落,組織進一個更大的架構裡面。這種寫法可以每日按進度逐漸積累,較不耗神,膾炙人口的《地圖集》就是代表。
不過自從《體育時期》之後,他發現這種工廠生產線的作業方式無法承載一個宏大完整的虛擬世界;而那種世界的創造,卻要求他得全神貫注,每天過兩種甚或四種人的生活,就像一個演員似的。畢竟寫小說是一種文字的表演,更何況教寫作也有沮喪的時候,「如果教的是『保底班』,有時真得從寫字教起。若要學生們自由發揮,結果可能還是寫出一模一樣的東西,比如說想做李家誠,或者要『做低』李家誠。如果面對是『拔尖班』,學生們很快就會抱怨你教的東西對考試沒幫助,因為他們以為這是堂補習課。」
所以在寫《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時候,他放棄教書,也不寫專欄短篇,專心一意地閉關練功。直到最近完成了「自然史第三部曲」的第二部,他才捱不住停下來出市區重新幹起那教書的勾當。
「還好家人都體諒,弟弟又能照顧家庭,母親雖不大懂我到底在幹什麼,但偶而看到報刊的評論還是會覺得我應該在做些有意義的事吧。其實我有很深的愧疚,每天看到身邊有那麼多人勤懇工作,就懷疑自己憑什麼可以如此悠閒。我知道很荒謬,可是我因此反而覺得自己一定要寫得更好,好像唯有如此方能還債。」
認識董啟章十年了,也讀過他每一本著作,今天是我們第一次「講金唔講心」。突然想起老好日子的作家如里爾克都是有「贊助人」的,那些財主也因此留名後世。要是我有三十萬可以贊助董啟章幾年,要他寫書還債,那叫划算。
朋友把這篇文章傳了給我看,說,看了很心酸,真的很酸。
於是朋友第二天就到書局買了《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好好來看。
我也轉貼在此,讓更多人讀。
如果有更多人因此而用行動支持一些值得支持的人與物,
或好好買一本,讀一本很值得去看的書,真是美事。